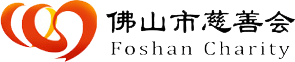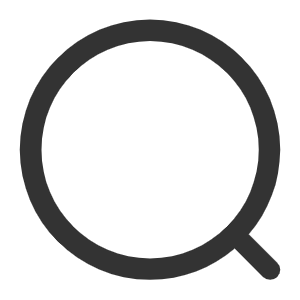公益创投,作为一个新兴的概念在我国出现了超过十年,但无论是在学术研究之中还是在实务操作的层面,对它的含义与指向仍未取得共识。本期专题,正是希望为公益创投在中国的实践进行一个简要而宏观的回顾,并尝试展望其前景。
回顾这十年,可能很多人要问的第一个问题,是公益创投何以在当代中国出现?就其时间节点而言,以“公益创投”为关键词的社会组织和公益大赛最早分别出现于2006年和2009年。在2012年前后,公益创投大赛这种形式在一批东部沿海城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。不难看出,公益创投的实践在当代中国出现与兴旺,与此期间提倡的社会治理创新息息相关。
在社会治理创新的话语体系之下,公益创投在中国从一开始就以项目购买为主要内容。在公益创投出现之前,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社会服务早已出现,但当时的购买,经常有找不到社会组织来承接的问题。此外,由于服务需要的认定自上而下,到了基层有时往往不接地气。凡此种种,使公益创投的概念显得格外吸引,无论是“关注初创型社会组织”,还是“强调服务需要由基层提出”等,均被寄予了补充既有购买格局的期望。
然而,在一场场公益项目大赛隆重揭幕、社会组织奔走相告之际,公益创投本该如何,实务界似乎无暇顾及。
在西方,以公益创投的方式来培育社会组织,启迪自市场部门中的风险投资。现在大家熟知的微软、雅虎和脸书等科技企业,一开始便是依靠硅谷的风投基金资助成长起来。资金的投入,当然要基于优秀的项目,但终极目标是让运作项目的企业发展壮大。以类似的逻辑反观公益创投,有两点值得一提,首先是投资方应该既有政府也有民间基金会,其次是投资项目只是手段,终极目标始终是帮助社会组织从初创走向成长。可惜的是,在中国式公益创投之中,资金多来自财政,其使用有严格的规范,于是主办方常把项目的评估结项看得比组织的能力建设更为重要,结果是公益创投的指向出现了明显的偏差。
有些大赛举办了一两年,发现交上来的项目书质量参差,为图省事,主办方干脆先拟出一堆题目出来让社会组织依样申报,搞“命题作文”。理论上,公益创投就是要由下而上地发掘服务需要,“命题作文”等于直接抹去这一优点。又例如“选强选优”还是“扶新扶幼”的争论,理论上很明确,实践中却多是另一种结果。看着公益创投的有限资源,流向实力雄厚的社会组织而不是草根组织,有时很让人神伤。
值得庆幸的是,随专业社工的加入,公益创投也的确是有力地撬动一批民间力量。通过比较基金会、民办非企业单位(简称“民非”,现称“社会服务机构”)以及社会团体这三类组织在所有社会组织中的比例,笔者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。2011到2015这五年间,全国的社团及民非的绝对数字上升,但各自占比却此消彼涨:社团从55%跌到不足50%,民非则从44%升至49%。然而在广东,无论是省还是穗鹏二市,此趋势正好反过来。五年间,广东的社团占比缓慢上升,民非占比则徐徐下跌。
这种倒过来的情况,最好的解释便是公益创投。大概2011和2012年开始,珠三角各市先后推出多个公益创投大赛,虽然到最后,拿到大头经费的仍是民非(例如社工机构),但有相当一部分社团借此机会获得资源,后者的注册数因而激增。倘若仅靠自上而下的的政府购买,各类草根社会组织(尤其是社团)极难在招标中拼得过已站稳阵脚的大型民非,这种“逆生产”态势绝不可能。
值得思考的是,广东的情况能否观照未来几年的内陆?放眼五到十年,若广东的情况以某种形式在中西部地区涌现,其作用可能正是增强已有民非及刺激社团新增。
公益创投的中国实践,资源多数来自财政,主办方的关注多在项目而非组织,这两点均或多或少偏离了主旨。值得安慰的是,随着同工的加入,慢慢地扭转着这些偏离:基金会在不断加入,社会组织的数量也在稳步上升。诚然,数量上升不等于体质增强,在略作安慰之余,作为公益创投应有义之的组织培育功能,仍须社工界同仁一直铭记并且不断尝试。
陈永杰
英国约克大学社会政策与社会工作哲学博士
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教授